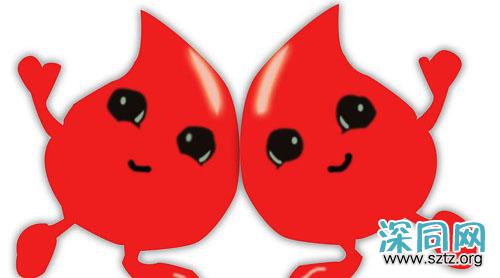让艾滋病走向终结
时间:2019-12-31 22:35出处:防艾阅读:139 编辑:@www.sztz.org
每个国家在积极研发和应用防治艾滋病的新科技成果的同时,或许也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防控措施,制订相应政策,形成对艾滋病的综合防治方案。

王月丹
美国研究人员领衔的科研团队获得一种艾滋病病毒新毒株的基因组序列,在艾滋病病毒相关命名准则发布19年后首次确认新毒株,相关论文发表在不久前出版的美国《艾滋病杂志》上。研究人员称,这一发现有助于他们走在变异中的病毒前面,从而避免出现新的流行病。
另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球约有379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2450万人正在接受治疗。随着治疗工作持续开展,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人数有望进一步下降。
世界卫生组织也宣称,到2030年,要彻底终结艾滋病传播。那么,随着相关科技的发展,艾滋病的终结是否不再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想?
艾滋病防控路漫漫
时间回溯到1981年。那一年,美国疾控部门在迈阿密连续收到了多个奇怪的感染病例报道,这些患者身上出现了十分罕见的肛门周围脓肿、肺孢子虫病以及卡波济氏肉瘤(一种十分少见的血管内皮细胞肿瘤)。突然出现的这一组罕见病患者,让美国疾控部门的官员和医生十分不解。随着研究的深入,谜底被慢慢揭开,它就是20世纪末的“世纪瘟疫”——艾滋病。
“艾滋病”是人类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的中文音译,具体指患者感染了人免疫缺陷病毒(HIV)后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缺陷所引起的一种综合征,患者常常会因为艾滋病的感染或肿瘤等并发症而死亡。
根据基因组的同源性不同,可以将HIV分为HIV-1和HIV-2两个类型,二者的DNA序列同源性只有40%左右。
其中,HIV-1于1983年被发现,是传播最为广泛和感染人数最多的一个类型,欧洲、亚洲和美洲等地区的艾滋病患者主要是HIV-1感染者;HIV-2于1986年被发现,其感染者主要集中在一些西部非洲国家,它通过性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的能力较HIV-1低,潜伏期也较长。
令人担忧的是,研究人员近日又发现了一个新的HIV毒株,这是近20年来人类第一次发现新的HIV毒株。这是否进一步提醒人们,HIV在不断变化,继而会对HIV治疗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虽然人们对这种新HIV毒株的传播途径及其对抗HIV药物的敏感性等细节问题还知之不多,但幸运的是,这份被称为CG-0018a-01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01年,此后多年并未发现有广泛传播迹象,这可能提示该病毒的传播感染能力要远低于HIV-1和HIV-2。
在与艾滋病的斗争中,人们从最初的恐慌和无助,到逐渐明确了HIV的传播规律和传播途径,继而通过规范输血和倡导健康安全的性行为等方式,切断HIV的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实现了艾滋病的可防与可控。
1996年,美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等人提出了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AART),人类抗击艾滋病的新篇章由此翻开。该疗法是联合使用三种或者三种以上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单一用药产生耐药性的风险,并抑制HIV的复制,即著名的“鸡尾酒疗法”。
鸡尾酒疗法,可使患者体内的HIV载量大幅下降,外周血(除骨髓之外的血液)内的CD4+T细胞(主要功能为免疫抑制)数量大幅回升,部分甚至全部恢复患者的免疫功能,延缓艾滋病的发病进程,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HAART的出现,大大改善了艾滋病患者的预后(根据经验预测的疾病发展情况),使艾滋病日益成为一种可控的慢性疾病。
不过,虽然近年来HAART治疗发展迅速,艾滋病患者的预后改善明显,但患者仍需长期服药,才能抑制体内HIV的复制。在这个过程中,患者需要数十年如一日地每天坚持服药,只有保持良好的依从性和服药习惯,才能减少HIV的耐药性产生,维持病情的稳定。
一旦患者没有坚持服药或者HIV产生了耐药性,就可能会使病情急转直下,最终导致患者的死亡。因此,依靠HAART治疗维持艾滋病患者的疾病稳定状态,依然算不上是治愈艾滋病。
那么,要治愈艾滋病,究竟路在何方?
代表性治愈路径:基因疗法
1996年美国科学家发现,欧美国家有一群人对于HIV具有天然免疫力。这群人即使接触了HIV也不会被感染。
研究结果表明,当HIV感染人体的CD4+T细胞时,不仅需要识别CD4分子作为病毒结合宿主细胞的受体,而且需要一个被称为CCR5的细胞表面膜分子作为共受体。当编码CCR5基因发生一种被称为Δ32的突变时,就会出现CCR5分子蛋白异常而无法参与介导HIV对T细胞的感染过程。因此,具有该CCR5基因突变的人就成为了HIV感染的天然免疫者。
对于艾滋病治愈之路来说,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2006年的德国柏林。当时,柏林有一位名叫布朗的美国人,他是一名英文教师,也是一名男性同性恋者。1995年,布朗及其情人被发现感染了HIV,随后的1996年布朗开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治疗,病情一直都比较稳定。
但在2006年,布朗又罹患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因此开始同时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和抗白血病化疗。随着病情的恶化,布朗离死神越来越近。此时,柏林大学医学院的胡特医生为布朗进行了骨髓干细胞移植,被移植的干细胞来自一位有CCR5基因Δ32突变的供者。
经过这种干细胞移植,布朗体内重建了对HIV天然免疫的T细胞系统,艾滋病和白血病的症状都得到了缓解,甚至停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也不会出现外周血HIV感染的现象。后来通过各种检查,在布朗体内的血液和各种组织中,均未能检测到HIV的感染。2009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布朗的案例,并确认他是第一位被治愈的艾滋病患者,这就是著名的“柏林病人”。
2016年,一个来自英国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一位患者的病例,该患者被称为“伦敦病人”。在这个病例中,一位被HIV感染的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接受了来自一名与他配型相符的CCR5-Δ32突变供者的干细胞移植治疗。经过干细胞移植治疗后,“伦敦病人”的霍奇金淋巴瘤和艾滋病都得到控制,即使连续20个月停用抗HIV药物,在体内也检测不出HIV的存在,复制了“柏林病人”的奇迹。
然而,由于CCR5基因Δ32突变的发生非常罕见,其在欧美人群中的纯合突变(一对等位基因都存在突变)率仅有1%,在中国和日本等黄色人种中这种突变的机会更少,考虑到MHC(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配型的问题后,HIV感染者找到合适干细胞供者进行治疗的机会十分渺茫。
不过,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CCR5基因Δ32突变供者干细胞来源稀少的难题已被攻破,这归功于基因编辑技术。目前,人们可以利用DNA编辑技术,将来自宿主自身干细胞中的CCR5基因进行编辑,使其失去与HIV结合的功能,从而获得对HIV感染的天然免疫力,然后再将编辑后的干细胞移植入艾滋病患者体内,从而实现治疗艾滋病的目的。
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染病专家巴勃罗·特巴斯和来自中国的解放军307医院的陈虎教授分别于2014年和2019年,利用锌指核酶技术(ZFN)和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CRISPR)技术,对HIV患者的免疫细胞或者干细胞进行CCR5基因的编辑后进行了回输或移植,取得了良好效果,即降低了HIV的病毒载量或使患者的病情得到了缓解。
此外,人们还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将已经整合到宿主细胞基因组中的HIV序列从基因组中清除掉,消除HIV感染的持续潜伏状态,从而实现HIV感染的完全治愈。
挑战依然严峻
虽然人类不断在HIV感染的预防与治疗领域取得突破和进展,但是,相关难题依然棘手,挑战依然严峻。
HIV可以感染人体CD4+T细胞,而该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活化与调节的核心细胞,担负着启动适应性免疫应答、维持免疫记忆效应和调控免疫应答过程的重要功能。
与很多人的猜想不同,在HIV感染过程中,特别是感染的中早期阶段,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可以产生针对HIV的免疫应答的,包括特异性的抗体应答和CTL(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应答,并对HIV在体内的感染发挥一定的压制作用,因此在HIV感染者的潜伏期,其体内的HIV抗原并不容易被检测到。
但是,随着HIV感染的发展,破坏的CD4+T细胞数量越来越多,机体的免疫功能严重下降,对HIV本身的免疫应答能力也会下降,最终导致HIV大量复制,患者进入艾滋病期,最终因为感染或者肿瘤等并发症而死亡。
HIV感染对免疫系统损伤的这种特点,给其疫苗的研发带来了很大困难。虽然目前人们已经获得了多个可以中和HIV感染的抗体,但是相关疫苗的研发一直困难重重,在多个HIV疫苗的试验研究中,均无法获得对HIV感染的持久性保护性免疫。从这个角度来看,HIV疫苗的研发,不仅要反复试验和摸索,而且还需要相关的基础研究,从理论上进行突破。
同时,在艾滋病的治疗方面,无论是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还是鸡尾酒疗法,都存在着治疗费用高、患者依从性差以及耐药HIV出现和增加等问题。而由于基因编辑技术仍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还存在着转染效率不高和编辑脱靶等技术性问题,临床大规模应用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并提升其治疗的精准度。这些都还需要科研人员和医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应对。
艾滋病和HIV感染者数量巨大,分布在世界各地,而各个国家的国情和经济发展又极为不平衡,正如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近日所言,艾滋病防治成绩在全球不同地区差别很大,其中涉及文化、宗教、经济、社会制度和性取向等多重因素。
因此,每个国家在积极研发和应用防治艾滋病的新科技成果的同时,或许也都需要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防控措施,制订相应政策,形成对艾滋病的综合防治方案。
(作者系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
来源:2019年12月25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6期